|
正常白斑图片 早期 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自缢在北京机电研究院家属宿舍楼家中,人们发现他时,身体早已经冰凉僵硬。 对于陈掖贤的自寻短见,他的同事却说这在意料之中。 当时人们普遍把他的死因定性为性格问题,也就是说陈掖贤自缢,他本身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显然,陈掖贤的故事背后,远比我们看起来的要曲折离奇。 熟悉笔者的人知道,笔者从不费笔墨在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身上。 那么,陈掖贤是谁?他的背后又有怎样坎坷曲折的经历与悲惨的命运呢? 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唯一合影 陈掖贤,生母赵一曼,熟悉红色历史的读者自然知道这三个字于我党的意义。 赵一曼曾是我党在东北最优秀的地下党员,也是我党最忠勇不屈的女烈士。 当惊悉赵一曼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害时,陈毅曾为其扼腕赋诗: 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聂荣臻,董必武等也相继写文、赋诗纪念这位我党最忠贞优秀的女娇娥。 多年之后,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等更是多次感怀赵一曼的牺牲,多次问及其儿子陈掖贤的状况,对陈掖贤给予了极大的关怀,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由此可见,赵一曼在我党的份量。 赵一曼,1905年四川宜宾县生人,与我党绝大多数的革命干部贫困的家庭出身不同,赵一曼生于晚清一个富裕的地主人家,但是她却能够在享受到优渥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发现底层百姓的疾苦与人民的不平等,并最终为此不惜离开封建家庭,成为我党一名最优秀的革命干部,这是一件极其罕见又难能可贵的事。 1926年,赵一曼的因其较高的思想觉悟,且在宜宾领导的组织工作特别优秀,正式成为一名饱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并开始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1927年,我党为了更进一步地培养一批能够任事、担事的干部,派遣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赵一曼成为当时极为罕见的女学生,正在此列。 1928年,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邂逅了一位湖南俊小伙陈达邦,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于同年4月份结婚。 赵一曼与丈夫陈达邦 两人结婚后不久,赵一曼便怀有了身孕,原本正是应该安心养胎的时候,可赵一曼不仅一边刻苦地学习,一边还要不遗余力地进行相关方面的组织工作。 1928年冬,因为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我党开始召赵一曼回国领导组织敌后建设工作,赵一曼又偷偷地向组织与自己的丈夫瞒下了已有身孕一事,就像没事人一样地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1929年夏天,陈达邦收到一封自己大哥陈岳云的来信这才知道赵一曼当初瞒下已有身孕之事,并于当年春天为其诞下一大胖小子,正寄养在大哥家中。 俗话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也许正是因为缺少母爱的滋润,才使得陈掖贤内心最深处的世界寸草不生,并给他带来了自戕的祸患吧! 赵一曼生下陈掖贤后,便整个人扑进了东北地区的地下组织领导工作。她的心中似乎早已经在个人小家与家国民族的大家之间做出了抉择。 在东北地区领导我党的地下工作时,赵一曼始终不顾个人安危革命在第一线,并相继担任了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政绩相当突出,根据地的人民都亲切地尊称其为“我们的女政委”,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们更是对其寄予重望。 当然,太过扎眼的革命活动,自然意味着日伪政府方面对其恨得牙痒痒,伪满政府直接在其内部报刊将赵一曼宣传为我党在哈尔滨最活跃重要的“红枪白马”女将军,欲除之而后快。 1935年11月,在一次领导与伪满日军的战斗中,赵一曼不幸腿部受伤而被追来的日军俘虏。 在狱中,赵一曼可谓是见识足了日军层出不穷的逼供伎俩。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敌人残忍地在这位年仅30岁的女娇娥身上施以鞭刑、烙烫、辣椒水、老虎凳、竹签刑,乃至电击都用上了,赵一曼依旧紧紧地咬住了腮帮子未吐半个字。 后来,恼羞成怒的日军直接放弃了逼供,索性对其拳脚相向以泄私愤,赵一曼疼痛难忍,奄奄一息之中,终于被日军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 在医院中,赵一曼又运用自己卓越的口才,从民族大义出发策反了贴身看守与照顾自己的警察与女护士,并在两人的帮助下逃出生天。 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赴抗日根据地的路上,因为全身伤痕累累行动不便,再次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抓回去。 抓回去之后,日军为了泄愤,对赵一曼更加残忍冷血地施以了各种暴行。但赵一曼始终忠贞不屈,日军方面最后只得作罢,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并游街示众。 1936年8月2日,珠和菜市口聚集了无数人,其中不乏我党意图寻找机会营救赵一曼的同志。 但相关方面一眼看出这是敌人布下的有去无回的圈套,因此同志们只能在角落里暗暗憋着劲儿,把这份仇恨埋在心里,目睹了赵一曼同志英勇就义的整个过程。 行刑时,有一位日本军官最终也为赵一曼的精神与意志力所折服,走到赵一曼面前说:“你还有遗言么?” 赵一曼 赵一曼则用凌厉的眼神狠狠地扫了一眼这位帝国主义分子说:“把这张纸条,传给我家乡的孩子!” 话音刚落,赵一曼便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年仅31岁。 了解历史的朋友知道,黑龙江省是我党最早解放的一个省,而哈尔滨市则是我党最早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后来我党更曾把哈尔滨称为“东方莫斯科”,将之视为首都的第一备选方案。 因此,作为最早期组织领导我党在哈尔滨地下工作的同志,赵一曼的死对我党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毛泽东在知道赵一曼慷慨就义的噩耗后,沉默良久后只能沉重地报之以“女中英杰”四个字,十分无奈。 这样一位女中豪杰,注定在我党乃至新中国的征程上永载史册。 她忠贞而顽强,为了同志的安危与革命的胜利又不畏牺牲,不屈不挠。她是我党为民族独立不畏艰险奋斗向前的最好印记。 而赵一曼牺牲时,儿子陈掖贤已经七岁了,然而这位懵懂之中的孩子却对自己母亲的死讯知之甚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是干什么的,长什么样。 因为当初赵一曼与陈达邦分开时,两人大吵一架并从此决裂,陈达邦后来便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陈掖贤自出生没多久,便被寄养在自己的伯父陈岳云家中。打小缺失的母爱与父爱,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娃娃心智的健全。他的内心始终有一大块是缺失的,并在慢慢长大时,感觉到了一种被区别对待与寄人篱下的孤独感。 陈掖贤 渡江战役之后,湖北解放,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任弼时同志爱人)第一时间找到陈掖贤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桀骜不驯但性格极其内向的大小伙。 据说当年负责处死赵一曼的那位日军军官极重信义,后来真的将赵一曼给陈掖贤留下的那张纸条想方设法转交给了我党。 1949年,这张纸条也被陈琮英一起带来,交给了陈掖贤。 纸条用极其仓促又充满死一样窒息气氛的笔法这样写道: “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在姑姑又给陈掖贤讲述了母亲赵一曼为了民族英勇奋斗的整个历程后,陈掖贤竟找来了蓝墨水用针挑着在右手胳膊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大字。 他虽内向,亦显偏执,但他对母亲的崇拜与爱戴,是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因为母亲赵一曼的缘故,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又特别优恤烈士遗孤,陈掖贤在组织的亲自关怀之下被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1955年,陈掖贤从人民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院任教。 当时我党考虑赵一曼同志对我党的贡献特别巨大,加之陈掖贤特殊的成长环境实在不易,中央又特意给陈掖贤拨了一笔关于其母亲不菲的抚恤金。 然而,这时候的陈掖贤的骨子里却因为母亲对其影响的缘故似有偏激,他固执地认为母亲为了民族大义而奋斗牺牲,是无比光荣伟大的,是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因此,他坚定地拒绝了领这笔我党出于关怀的抚恤金。 然而,一面是思想上的十足狂热与激进,另一面却是在理财上捉襟见肘,在自我生活料理方面更是窘况百出。 不幸的童年与压抑的成长环境让陈掖贤的性格里充满了自卑、偏执与放荡不羁。 他既不善与人交流,也不善于照顾自己,缺少亲情温润的他更是养成了放任自流的习惯,不仅生活上得过且过,在理财上更是寅吃牟粮,毫无计划。 参加工作后没多久,陈掖贤便与自己的学生张友莲坠入爱河,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很快又生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那时候组织上给陈掖贤的工资是每月69月。在那个2块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周口粮支出的年代,这笔收入已经不菲,乃至走到了大多数国人的前面。 按照正常开支来说,即使一家四口一个月40元左右的开支,也还可以有29元左右的富余可以改善生活。然而陈掖贤的生活状态却是每到月底都要借款度日。 他极不善于理财,又大男子主义不愿意把工资交给妻子,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说,一贯就是发了工资月初大手大脚猛吃海喝,月底前一周一家四口无米下炊只能靠小额借贷度日。 后来,他的妻子张友莲参加了工作之后,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元,然而仍旧丝毫没有改变陈掖贤家每到月底经济捉襟见肘孩子嗷嗷待哺的状况。 陈掖贤的许多同事回忆,那时候每到月底总能听到他们家传来夫妻二人的打骂声与娃娃的哭闹声,显然是妻子张友莲劝诫丈夫节制花钱而不得大打出手。 1960年,压抑的生活环境与彼此的隔阂终于促使得张友莲向陈掖贤提出了离婚。离婚时,张友莲几乎已经被生活逼得精神抑郁,经常自言自语。 陈掖贤与同事 1956年,陈掖贤所在的北京工业学校被改建成了第六机床厂,袁宝珊曾与陈掖贤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到了1981年,她是最了解陈掖贤状况的人之一。 据袁宝珊回忆,陈掖贤与张友莲结婚之初,组织上对其可谓是特别照顾,大多数人的单位房都是背阴在四到五层的,只有极少数的干部为了工作需要被安排在了一层。陈掖贤当时是极其罕见地分配到了一层的非干部人员,并且他的房子还是向阳的。 提起陈掖贤的经济问题,袁宝珊也是抓耳挠腮苦恼不已。 1960年3月,陈掖贤与张友莲已经离了婚,孩子都送到了亲戚那里。袁宝珊与陈掖贤当年同时被派到楼梓庄公社劳动锻炼。这段时间又苦又累还没有吃的,因为是邻居,所以袁宝珊对这位不善于照顾自己的老哥哥尤为关心,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比常人深厚的友谊。 劳动锻炼回来之后,组织上鉴于陈掖贤在劳动锻炼期间能吃苦耐劳的表现,又把他的工资涨到了77元每个月,但是陈掖贤在每个月给女儿寄去二十多块钱之后,近六十块钱傍身的他竟是不够用,依旧是每到月底就没钱吃饭了。 有一次月底,学校领导看陈掖贤几天都没有去上班十分着急,便特意赶去他家里看他,这才发现陈掖贤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只能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后来组织上鉴于陈掖贤的特殊情况,又找到袁宝珊商量,组织上把工资先交给袁宝珊,由她代为分配陈的支出,由学校监督,此事原本也得到了三方的一致协商通过。 刚开始的时候,袁宝珊把陈的工资每月分为六份,第一份先给他的孩子。第二份则是还清他每月的借款并备足一个月的粮票。剩下的四份,每周给一份作为他的零花钱。 刚开始还行,可没多久陈掖贤便管不住消费的冲动,屡次就提前支配零花钱而和袁宝珊争吵。 袁不给,他就又有了新点子,先找私人借贷,到了下次月初再按照约定还回去。如此一来二去,恶性循环,根本治标不治本,组织上为此十分苦恼,代为管钱的计划只能破产。 袁宝珊有一次忍不住问陈掖贤:“陈掖贤同志,咱不说过去的事,你能和我说说你上个月花的钱都哪里去了么?” 陈掖贤则不以为然地首次吐露了自己花费项目,直接让袁宝珊惊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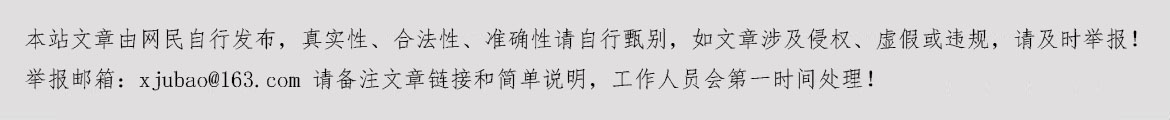
|